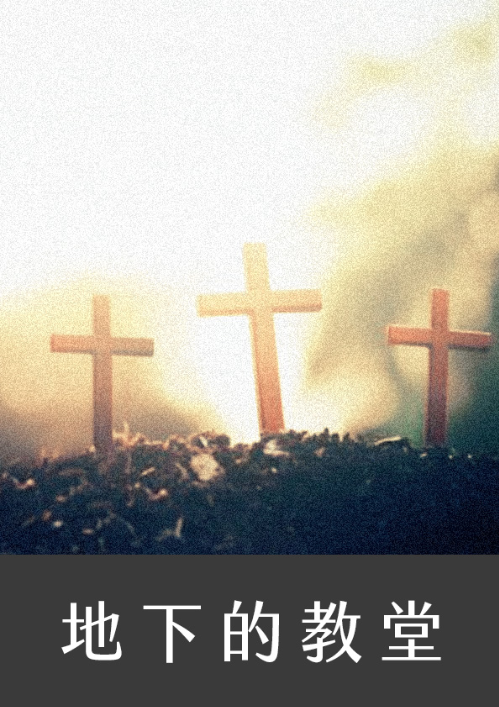立即閱讀:《千紙鶴:秘密》
立即閱讀:《千紙鶴:秘密》
甘弟本名邱宗翰,寫有《百工之人》、《千紙鶴》等社會議題強烈的長篇小說。身為小說家,他積極介入現實,用文字直逼各種議題,包括核安、廢死、長照等。然而,如此入世的寫作姿態,其實來自他出世般的苦行生活。
過分認真的甘弟,使他的寫作與生活都成了修行。
他曾閉關四年,斷絕與外界所有聯繫,每天只寫小說,用腦過度,患上頭痛毛病;他奉行永續和諧理念,吃全素,還有全套環保器具,環保吸管、環保筷,以及三組環保袋交替使用。待人接物他也一貫決絕。朋友酒駕,他送對方一組佛教樂器——磬,希望友人振聾發聵。豈料對方再犯,他便與之決裂。
 甘弟在補習班教國文,他說自己是「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」,透過講述一個個故事讓學生對知識與世界充滿好奇。
甘弟在補習班教國文,他說自己是「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」,透過講述一個個故事讓學生對知識與世界充滿好奇。
對此,甘弟只說:「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。」結果是他的朋友少到結婚時只發了四張男方親友喜帖。孤獨的時候,他用寫作頂住大而殘破的世界。其實,他身殉文學的態度,從筆名就看得出來。
小說是自我追尋之路
訪問一開始,我便好奇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筆名從何而來。聊著聊著,我們岔題了,甘弟復主動提起這個問題。他說來源有三,首先是他的精神導師──甘地。他用這個名字寫作,希望每次見報都像在宣揚甘地的精神。此外,「甘」也來自《阿甘正傳》男主角──阿甘母親要阿甘遇到問題時就往前跑,他便跑了一生的長度,「很多人覺得阿甘很笨,但我覺得這是堅持,不是笨。」就連筆名也是他自我砥礪的工具。至於最後的弟字,則是因為他是家裡的老么。
甘弟現於台中教補習班。之所以選擇補教業,也是因著寫作,「這是花最少時間可以獲得最多金錢來支持我寫作的行業。」甘弟總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:「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」。然而,說書人想說的是自己的故事,「在課堂上我說故事,但不是我想說的故事。既然我教書已為了迎合市場,寫作時我只想寫自己想寫的。」
正因如此,甘弟筆下的故事儘管千迴百轉,仍往往是自我追尋與辯證的過程。長篇《百工之人》講童年悲慘的撿骨師意外尋得生父遺骨,既尋回自己的前半生,也為作惡多端的父親贖罪;《千紙鶴》藉一樁老人院命案帶出母女和解的故事。命案不是重點,案件周圍的情理才是小說家著力之處;愛與孤寂與失落,放在罪與罰的天秤上,該如何衡量?《千紙鶴》裡看似難解的習題,卻成為甘弟目前最滿意的作品。此外,還有短篇〈地下的教堂〉、〈凱達格蘭的獨舞〉、〈有福〉等,分別聚焦勞工、蘭嶼核廢料、核安議題。
寫出蒙塵角落的故事
甘弟的小說總可見若干社會議題,他說自己最崇拜托爾斯泰,寫作是「用文學記錄社會運動,把很嚴肅的議題說得很精采。」他住在圖書館附近,不是在埋頭寫作,就是在圖書館翻文獻找資料,或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。
我提到他的若干小說讓我想起黃春明,同樣聚焦底層,也往往讓他筆下的小人物在黑暗中一步步通向有光的所在,「上層的成功故事天天都在流傳,底層發生什麼事卻沒人看見。如果我不去寫,可能就沒有人在乎了。我甚至想寫動物的故事,為動保說話。」
 「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。」甘弟把自己的生活與寫作都變成了修行。
「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。」甘弟把自己的生活與寫作都變成了修行。
是否透過小說向讀者灌輸自己的價值觀?甘弟說,「我想呈現真相,寫完後我自己會有答案,至於讀者,就讓他們自己領會。在我的小說裡,沒有主要的聲音,每個角色都有發言權。」好比《千紙鶴》裡的法庭攻防涉及死刑議題,甘弟承認自己支持廢死,「我不怕讓人看見自己的觀點。做一個負責任的作家,必須有勇氣提出你認為對的答案。」
於是,我們談到文學如何與現實重疊,小說太貼近現實,是否便成新聞照抄,以及小說會不會與非虛構文學沒有了區別?「當現實與戲劇性衝突時,我會選擇後者。對我來說,報章雜誌仍有破口,得透過小說去探索。」我想起佛斯特在《小說面面觀》裡申明的:「小說比歷史更真實,因為它超越了可見的事實。」相較於真實,甘弟同樣追求說故事的力量,「故事只要存在,世世代代的人都會讀,藉此回到那個時空。」甘弟說,他的小說與非虛構文學分進合擊。
甘弟用小說發聲,但小說的力量在當代恐怕已式微。我們聊到台灣近期以文學改變社會的例子,兩人腦中頓時一片空白。不過,甘弟舉了一個反例。幾年前加拉巴哥象龜亞種之一,平塔島象龜僅存的「孤獨喬治」死亡,該物種遂宣告滅絕。許多人以此為創作主題,看起來是悼念一個物種的消亡,然而更多是因為「孤獨喬治」帶來的孤寂感太過強烈,讓人浮想聯翩。甘弟說,文學處理議題不免走向抒情,最後往往也只能抒情式結束,他自己則儘量避免讓小說流於濫情的同情。
或因如此,寫作路上的甘弟是孤寂的,他說自己寫小說沒有市場考量,冷門也沒關係,「我是我自己最忠實的讀者,因為我寫的都是我自己想知道的事。」
創作是歡愉也是贖罪
甘弟的創作之路有自我質疑,也有至高無上的成就感。他說寫小說可以給他極大的快樂,「我只是在抄腦中跑出的文字,彷彿我身在其中,聽到小說人物的對話。寫作讓我上癮,非常痛快。」他形容寫小說寫入神是「上帝親吻的時刻。」他的小說癮頭多重呢?甘弟當兵時在野地出任務,因為想寫小說,跑到連長的指揮所,戴著鋼盔,用NOKIA手機3310當光線就開始寫,同袍看到還嚇了一跳。
 甘弟關注時事,除了寫作,也上街頭;對他而言,兩者有同樣振聾發聵的效果。
甘弟關注時事,除了寫作,也上街頭;對他而言,兩者有同樣振聾發聵的效果。
不過,創作不是全然幸福的一件事。甘弟把生活過得像是修行,寫作對他而言,也是修行的一部分,「寫作對我是贖罪,既然苟延無恥的活著,就要靠寫作救贖。」
創作之於他的矛盾,或許從他筆下的女性可窺見一二,「我小說中的母親常常是妓女或癱瘓者,因為我的家庭非常複雜,我媽在酒店上班,我爸是警察,我有兩個姊姊,一個同母異父,一個同父異母,後來才發現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,我媽還有很多『叔叔』,我爸也有很多『阿姨』。我媽上班時間很晚,小時候看到她,她幾乎都在床上睡覺。」母親對甘弟來說,是難解的存在。他說母親有躁鬱症,全家不知該如何面對,便逐漸瓦解;獻給媽媽的小說寫完,想給她看,「但想起她帶來的痛苦,我猶豫了。」
小說家瑞蒙卡佛談人生,說:「對大多數人而言,人生不是什麼冒險,而是一股莫之能禦的洪流。」甘弟投身洪流,透過書寫,讓自己也變成洪流的一部分。談及他計畫中的大長篇小說《人造天堂》,是以巡禮各國各地的方式檢視人類的存在,也是他永續、和諧理念的延伸。
「我們製造了一個廢墟,要怎樣讓它變天堂?」這是小說家甘弟的天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