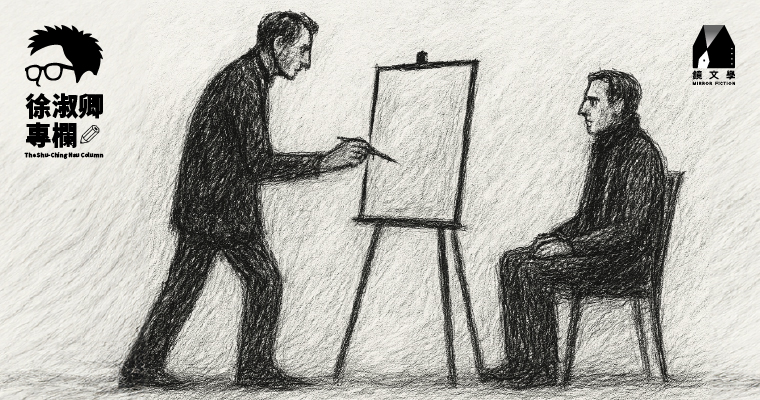
作者/徐淑卿
1965年美國作家詹姆斯·洛德(James Lord) 出版了《A Giacometti Portrait》,描述自己在巴黎擔任賈科梅蒂(Alberto Giacometti)模特兒18天的過程。這是首部作家以模特兒視角所寫的書,後來拍成電影《寂寞大師》。
電影許多場景在賈科梅蒂工作室,所以我們看到周圍散布他創作中的如〈行走的人〉那樣人體頎長的塑像。賈科梅蒂想為洛德畫肖像,他說,你正面看起來像惡棍,警察看到一定很感興趣。「但還好,我看到的跟我畫的不會一樣。」在這本書裡,洛德描述賈科梅蒂不斷塗抹修改,自我懷疑,認為自己永遠無法忠實呈現他所見之物。
也許「忠實呈現」注定就是無法抵達的徒勞,因為人始終在變動中。就像英國當代最重要肖像畫家盧西安·佛洛伊德(Lucian Michael Freud)也曾對他的模特兒,英國藝評家馬丁·蓋福特(Martin Gayford)說:「你每天看起來都不一樣。」
既然不可能所畫如所見,重要的也許是藝術家賦予人物的生命氣息。賈科梅蒂的作法是:「要讓頭像看起來真正逼真是不可能的。你越努力讓他像真的,反而會越不像真的。但既然藝術作品本來就是一種幻象,那麼你若強化這種幻象,就能更接近生命的效果。」
馬丁·蓋福特在2003年擔任佛洛伊德模特兒近兩年,完成一幅油畫〈藍圍巾的男人〉和一幅版畫〈頭像〉。在佛洛伊德去世前一年,2010年他出版《藍圍巾的男人》,這是繼《A Giacometti Portrait》之後,第二部作家以模特兒親身經歷所寫的書。
這部以日記體書寫的作品,不僅是畫家對模特兒的觀察,也是模特兒兼藝評家對這位著名肖像畫家的觀察,還有對於模特兒這個身份與畫作之間關係的思考。就像延續半世紀前賈科梅蒂與洛德的對話。
在這本書裡,肖像畫是否要寫實,一開始就被否定。佛洛伊德早年就說過:「與真人完全相像,不是、也不能是創作肖像畫的目的。試圖把自然的東西畫出來的畫家,只是依樣畫葫蘆的畫家。」
雖然「像」模特兒不可行也沒必要,但畫家在「變動不居」的模特兒身上想看到什麼?卻是始終縈繞在畫家與模特兒之間的問題。畫家有其想要趨近的「真實」,這與像不像未必有關;而模特兒也必然會在畫家的凝視中,忐忑不安,出現自我的縫隙。
蓋福特說,對於畫家的凝視,與其說不安,更像是疏離感。「它帶出了一個我們每個人在童年時期想到過,後來也不斷重複想到過的問題,就是這個叫作『我』的東西究竟是什麼?當然,這也就是肖像畫的核心之謎。」
還有,是否如「格雷畫像」那樣,揭示他不想為人所知的秘密?「不管是好是壞,我原來想隱藏的那些部分也許會就此展現在人前。」
「佛洛伊德身上兼具一個小說家的敏感和一個畫家兼容並蓄的觀察力。」蓋福特所感知的特質,他日後用了另一個形容「巫師」。
這是這本書非常有趣的地方。佛洛伊德與蓋福特不像一般畫家與模特兒那樣權力失衡,佛洛伊德在凝視蓋福特,蓋福特也在凝視他,佛洛伊德描繪蓋福特時,蓋福特也在書寫他,只是一個用畫一個用文字。
但是看這本書時,你會覺得佛洛伊德掌握全局。蓋福特所描寫的佛洛伊德非常有趣,他對佛洛伊德的個性、特質觀察入微,而且基於佛洛伊德對模特兒所喜歡的互動交流,蓋福特也記錄了許多佛洛伊德的故事。但這更像福爾摩斯身邊的華生,佛洛伊德是唯一的創造者,是那個吹一口氣讓人物活過來的人。
為什麼會讓人有這種感覺?也許是因為佛洛伊德強大的自我,使他的存在感格外分明。也許佛洛伊德以非凡的天賦,讓我們看到他如何「造就一個模特兒」的過程。蓋福特說:「對於佛洛伊德來說,他畫的所有作品都是肖像畫。他在藝術史上留下的與眾不同之處,就在於他對一切事物的個性的認識。」
但更有可能的是,蓋福特臣服於佛洛伊德的凝視之中。一方面欣然體驗作為模特兒這種「介於超覺靜坐和髮廊理髮之間」的過程,一方面也身歷其境思考「肖像畫」為何物?畫家如何創造出一個連模特兒自身也未能察覺的自己?
這的確有如面對巫師的神力。蓋福特說:「〈藍圍巾的男人〉有部分可以說是一幅畫出我為整個創作過程著迷的作品。我能從照片裡看出那種強烈充滿著興趣的神情。我看見畫裡的他正在看我。正如一幅好的作品可以同時表達多層意義,佛洛伊德本人的視角也在裡面。」
畫家與模特兒,常被視作凝視與被凝視的主、客體(蓋福特的用語是「被動的主體」),模特兒有時像是「物品」一般。但如果畫家與模特兒之間,有著多重的關係,這樣的位置就會複雜且多變。
2019年英國畫家西莉亞·保羅(Celia Paul)出版一本傳記《自畫像》(Self-Portrait),她是佛洛伊德畫作〈裸體女孩與蛋〉的模特兒,也是他眾多情人之一,和佛洛伊德生有一子。
西莉亞·保羅說,她想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是,「透過用我自己的話寫我自己,我把我的生活變成了自己的故事。特別是盧西安是我故事中的一部分,而不是像通常那樣,我被描繪成他的一部分。」
不論是在傳記或者是後來的畫作,你可以感覺在畫家保羅心裡,佛洛伊德的凝視永遠都在。甚至,她用幾十年的時間來準備回應。
她描寫第一次當佛洛伊德模特兒時,哭個不停。「裸體的經歷讓我失去防備。」 她形容那是一場折磨。佛洛伊德的凝視讓人難以承受。「我覺得自己像是在醫生面前、在醫院裡,甚至是在停屍房裡。」
但是,保羅本身就兼具畫家與被畫者兩種身份,她有大部分作品都是肖像畫,模特兒多是與她親近的家人。《自畫像》這本書也被解讀成是一連串與「坐畫」(Sitting,指擔任模特兒)相關的生命歷程。她曾多次擔任佛洛伊德的模特兒,佛洛伊德也曾擔任他的模特兒,她更多的坐畫是她的家人,如她的母親和姊妹。她母親第一次擔任模特兒時也曾哭泣,因為她覺得女兒將她當成物品。
保羅和佛洛伊德的關係維持了十年。佛洛伊德為保羅畫的最後一幅畫是〈畫家與模特兒〉,在畫中她正在畫一個裸體男人,她手持畫筆腳踩著顏料,這既是在畫中逆轉傳統的性別角色,也逆轉了〈裸體女孩與蛋〉觀看與被觀看者的位置。只是畫外的佛洛伊德看著她看著裸體男人,這似乎也預示了,保羅始終難以脫離佛洛伊德的注視。
關於這幅畫,保羅說,「盧西安願意以藝術家這個強大的位置來描繪我,令我感到榮幸,他的認可對我意義重大。」但她也感到一絲惆悵,因為她已經不再被描繪為慾望的對象。
夾雜著情人、孩子的父親母親等多重角色,保羅與佛洛伊德的關係,遠比畫家與模特兒更複雜。對保羅來說,這裡纏繞太多必須經過時間才能言說的情緒。她後來不斷以自己的作品來回應那種被凝視的處境,或說這段回憶。她在2012年也就是佛洛伊德去世後一年畫了同名的〈畫家與模特兒〉,裡面只有一位略有年紀,衣服滿布顏料顯示其畫家身份的模特兒。2022年她畫了〈幽靈女孩與蛋〉來呼應佛洛伊德1980年為她所畫的〈裸體女孩與蛋〉。
今年,在西莉亞·保羅於倫敦舉行「鬼魂的殖民地(Colony of Ghosts)」畫展前,挪威作家卡爾·奧韋·克瑙斯高(Karl Ove Knausgaard)發表一篇文章,他在2023、24年兩次採訪她。
克瑙斯高談到〈幽靈女孩與蛋〉這幅姿勢和構圖一樣,但意涵遠超過「致敬」的重製之作。他說,最令人著迷的差異,在於身體的存在感。「在保羅的畫中,肉體正逐漸消退,好像畫的不是現實,而是對那現實的記憶。」
「我們看到的是保羅的凝視,在看著佛洛伊德的凝視——凝視被雙重化了,角色也被反轉,從模特兒變成畫家。而保羅在此畫中,也在以佛洛伊德的筆法作畫——她正沿著他曾走過的筆觸,重走他的路。她成為了他:她是幽靈模特兒,他是幽靈畫家。」
也是在這篇精彩的文章中,克瑙斯高提出或許可以當作「畫家與模特兒」關係的洞見。模特兒當然是一種「物」,但在保羅的畫裡,坐在椅子上、躺在沙發上的人,(與畫家)進入了一段關係,那段關係本身,往往才是畫作真正的主題。
在《藍圍巾的男人》,蓋福特也有類似看法:「一幅肖像畫的真正主題也許就是畫家與創作對象之間的交流。」而在這樣的交流中,畫家捕捉到模特兒突出的特徵與情緒,而這或許就是肖像畫中成為永恆的一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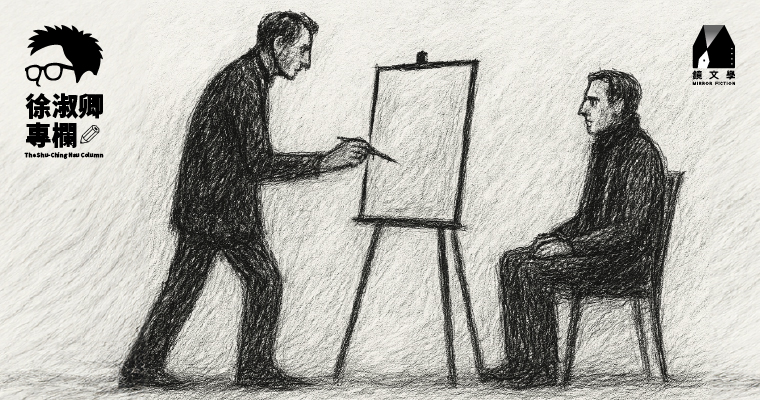
雖然「像」模特兒不可行也沒必要,但畫家在「變動不居」的模特兒身上想看到什麼?卻是始終縈繞在畫家與模特兒之間的問題。圖/顏一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