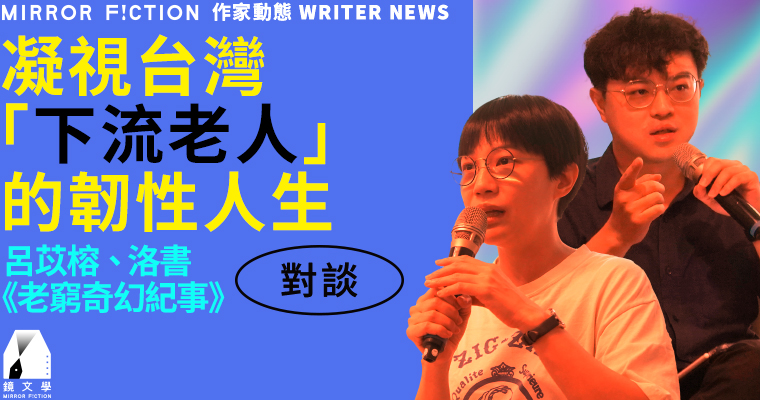歷史縫隙的文學之花──陳瑤華談《破浪: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傳奇》

歷史的空白,是文學介入施力的縫隙。對陳瑤華而言,寫作歷史小說便是以想像力補足史料中空白的過程。
在過往的小說創作中,陳瑤華呈現對於女性議題的高度關心。不管是書寫女性犯罪的《惡女流域》、處理演藝圈ME TOO事件的《錯身1998》,或與慰安婦記憶對話的《鐵百合》,皆試圖在社會事件或歷史題材中談出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。
《破浪: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傳奇》以真人真事為本,描繪清末艋舺、大稻埕繁盛商場的風起雲湧,也刻劃女性創業者如何在傳統年代為自身開闢道路。
以想像力為歷史增添血肉
談及前些日子廈門福建之行,陳瑤華笑稱是一場遲來的田調。旅途中不僅親臨小說人物橫渡黑水溝之路,也在馬尾船政博物館中細數各式船舶,想像清朝末年古老帝國的人們開始接觸洋務、科學,面向世界的歷程。她想描寫的女主角吳帆正以如此姿態立身於世,不固守既有的傳統榮光,而是盡力接觸外來的人物與技術,探索全新的世界。
陳瑤華由參加艋舺文史導讀的姐姐口中首次聽聞黃阿祿嫂的故事。雖是清末臺灣著名的木材、樟腦商人──當地甚至有諺語「第一好張德寶,第二好黃阿祿嫂,第三好馬俏哥」流傳其特殊地位──相關史料卻極為稀少,連夫家族譜都未曾載明這位傳奇性的三房。
史料的闕如成為陳瑤華想像力奔馳的起點:怎樣的女性可以帶著工人上山伐樟?如何解決男性主導的商業世界中的紛爭?保守時代如何以女性身分達致如此成就?她用寫小說來解答自己的疑惑。
裹小腳的大家閨秀難以穿過崎嶇的山路監督樟木開發,因而陳瑤華賦予黃阿祿嫂未經纏足的童年及風月場所查某𡢃的來歷,又令她擁有不囿於規範的獨立性格。就這樣,歷史上不具名姓黃阿祿嫂,在陳瑤華筆下化為「吳帆」,擁有立體的經歷與性格。雖然可能並非黃阿祿嫂的真實樣貌,卻是陳瑤華盡力發掘其可能性的結果。
學生時代的訓練成為她的創作養分。大學時陳瑤華先是就讀於歷史系,儘管對庶民史感興趣,當時的授課卻以政治史為主;因而她轉往中文系,企圖在小說中拼湊這些與日常相關的歷史。
過往歷史學的訓練使她得以找尋資料建構當時的社會環境,理解行郊組織、樟腦貿易等時代背景,從而將人物合理地置入其間。大量閱讀之外,陳瑤華也透過實際的踏查及訪談掌握歷史空間,在創作之餘遇見許多不同的人、累積額外的知識,這些都是後來的儲備。
好好寫作,好好生活,好好睡覺
創作小說時,陳瑤華自陳往往是人物先行,會為角色製作詳細的小傳,並讓人物帶領故事進行。塑造人物的性格、背景,也決定其說話的口氣、形象,在特定時刻為何會做出特定決定,從而掌握故事的走向。
她也提及,最早在創作純文學、短篇小說時,通常僅靠靈感完成故事。然而和鏡文學合作創作長篇的大眾小說時,由於被要求提交大綱,故會較有意識地預先架構故事。面對不同題材,她會斟酌敘事的趣味及讀者視角設計開頭,甚至會在故事完成後重新調動順序,令其達到更好的敘事效果。如在撰寫大眾不熟悉的歷史背景時,依時順敘讓讀者容易進入;談及台籍慰安婦時,則為了處理女主角被顛覆的認知及懊悔而採倒敘的手法;甚至採用穿越的形式,讓當代的年輕男孩回到90年代,和最終走向悲劇的女星對話、了解其心路歷程。
《破浪》的完稿過程也經歷了大幅調整。在初稿中,黃阿祿的故事占了萬字篇幅,但為了避免搶占故事焦點、令情節更快地進入吳帆商戰的橋段,而被編輯要求大幅刪改。陳瑤華半開玩笑地談起改寫時的情緒,卻也認為編輯可以據其經驗提供來自讀者的視點,幫助故事更容易被讀者接受。
寫作不免遇到瓶頸,對此陳瑤華的建議是「去睡覺」。「睡覺是一個很好的靈感來源,雖然腦袋放空,但是你的故事還是存在你的心裡面,」她說,「不要一直想著去填補空白的時間,因為靈感有時會在不注意的時候突然出現。」
她認為寫小說重要的是「真正地去生活」,因為寫作往往仰賴日常的積累,不僅是讀過的書追過的劇,還有對生活細節的感知與各樣情感的體會。
以自身為例,比起擔任老師的時期,在當全職媽媽的十年間,反而得以平等地和形形色色的人們交流,從觀察中獲得新的刺激。期間閱讀許多日本的女性大眾小說,也令其萌生創作大眾文學的念頭。比起文字雕琢,更重視故事本身與意念的產生。這段時期彷彿起跳前的蹲低點,為後來更高的跳躍累積能量。
提供一條可能的路徑
回望《破浪》的創作,陳瑤華自覺有些「女性勵志小說」的意味。當代女性也許不似當年受到許多傳統條規的束縛,卻仍不自覺地活在緣於性別的期待或歧視中。黃阿祿嫂的故事中草莽的精神或許提供了現代女性一條可能的路徑,去思考身為女人之前,作為一個單純的「人」,如何盡可能地突破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、完成所欲達成之事。
陳瑤華呈現出晚清艋舺、大稻埕的豐富多元,邀請讀者隨黃阿祿嫂的腳步,一同踏入這個充滿危機與轉機的精采時代。
撰文 李心柔 ◆ 攝影 鏡文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