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爱的有罪论──蒋亞妮读《亲爱的共犯》
米兰·昆德拉(Milan Kundera)在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里,写下:“我们在没有被忘记之前,就会变成一种媚俗,媚俗是存在与忘却之间的中途停歇点。”陈雪的新作《亲爱的共犯》逼近的核心,与它相近。与其说,这是一部悬疑小说、推理小说,其实它更是藉著一场绑架失踪案、借道小说中住在“白楼”里外的众人,将视线投向“媚俗”世间。像是以灯探照,什么是好、什么是爱,你的心真的为此震动吗?《亲爱的共犯》陈雪 著出版日期:2021/1/29与前作《无父之城》相同,故事始于一场失踪。这一回,住在“白楼”里显贵的张家三代,二子张镇东忽然被绑架,刑警周小咏展开调查。嫌疑者有财富、有爱情,当然也有妒恨,人类究竟会被什么驱动?当我们关心一个社会案件、当我们为了家人与爱情付出、伤痛、流下眼泪时,要怎么看待每一滴眼泪?眼泪,总有两种,第一种眼泪,是出于自己与对方的关系;第二种眼泪,却是因为仿佛能和“所有的人类”在一起,同悲悯共感动,如此美好丰沛,流下的泪。两种眼泪,都是爱,或以为是爱。这也是米兰·昆德拉告诉我们的:“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。”如果可能,请把这本小说里所有的眼泪与选择,看作第二种。只因为,这个世界目前的眼泪,都更贴靠后者。复调之式神陈雪的小说总像是课堂里没教的文学核心。奇技淫巧与理论形式,那些可以被书明、曾经被论述的典籍,先变作了小说作品(work),再变成我们所见真正的文本(text)。从作品到文本的逸变,是一种精神视线,作品是可见的,文本是不可见、不可被计算与评价的;作品会占据空间,文本则是一座方法场,我们只有透过创作过程,才能检验文本。曾有个被单一化到极致的人物,那位像是一生只说了一句“作者已死”的罗兰·巴特(Roland Barthes),其实他所知更多:“文本不只是符码、可见的物件,更是乌托邦、不可见及一个可流动的过程。”如此看向陈雪小说的轴心,尤其到了《摩天大楼》与《无父之城》后,更能理整出她小说的特长之处,课本里、理论上、简而化之的一个名词:“复调小说”。西方世界,从杜斯妥也夫斯基(Fyodor Dostoyevsky)、威廉·福克纳(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)的小说到《冰与火之歌》;东方与之相对,亦有《罗生门》及上溯至《红楼梦》、近身如凑佳苗小说般的复调蓝本。于陈雪的小说中,不管是此本《亲爱的共犯》里,间次地以失踪者张镇东身边之人开章分述,从引梦办案的刑警周小咏、生于微处的张镇东妻子崔牧芸、张镇东的大哥大嫂,到白楼里的管家陈嫂、外佣阿蒂⋯⋯全都成了陈雪指点江山的各种乐音。一如她在《附魔者》里,似以魂力捻出烛绳般,点燃所有在爱中的不同伤者与叛者⋯⋯直至《亲爱的共犯》,读者终于可以笃定知晓,小说家完全自知她与她的小说之技,有著如阴阳师与式神般最强大的契约术法,不论是复调、悬疑与人性,她都握于掌、晓于心。大象灰色的梦游者小说和爱情总是相近,最近之处,是明明知道所有的道理、做好一切准备,却还是写不好一本小说、谈不好一场恋爱。这便是“复调小说”一词,在课堂外的核心,在陈雪手中的别样,更是陈雪在经过了几年的文学高强度写作计画(字母会)后,意外地,将她的自我与小说浓淡度调低,从墨黑漂成了大象灰。小说中几次以颜色寓阶级,先是“白楼”那难以言说的白之综合:“只见得一片雪白、粉白、雾白,纷纷落落地营造出一种濛濛的光晕,阳光底下看起来,眼睛都要闪痛了。”再来便是“大象灰”,“这世上竟然有某些颜色是昂贵的⋯⋯大象灰,听起来不起眼的名字,那灰色若不是使用高级皮革,并且透过特殊的调制鞣制印染,不可能呈现出来,没有经过复杂的工法,最后只会变成老鼠灰。”陈雪的小说便似那法国最奢靡的皮革名店,凡俗者总被满柜的时装或前头的金工珠宝所诱,可那以Madame小牛皮、Epsom牛皮精巧鞣制而成的大象灰或班鸠灰,稳当地收在暗架,必得等候暗语、确认眼神,才能成为那识货人。它才是每个名字后的一生历练,如玉髓、岩脑与树之琥珀。这本《亲爱的共犯》可被视为影像的衍生空间,另一部独立于陈雪“空间三部曲”中“大楼”(《摩天大楼》)、“小镇”(《无父之城》)、“海岛”(尚未出版)写作版图外的作品。虽然,小说也极大程度的贴著“文明街四十五巷”那座白色大宅的空间伸展枝枒。但陈雪大幅地缩砍独白与呓语般的文字句式,把枝枒留给颜色、形貌、建筑与故事情节,这使得它的文字也变得近似一座建筑。透过指令、听闻线索,读者便成为了观众,小说中长出楼宅、看见人影,影视化的野心由此可见。没有野心的书写,难以成就伟大的作品与作家。每当作家一开始写作,作品就脱离了他自身,从陈雪的写作段落中,偶尔剥离如降灵般的感受,比如写梦论梦,醒觉而别致。小说中能以梦探案的刑警周小咏,这么说起她的梦:“如今的梦,都像是白天工作的延续。”、“她知道这不是托梦或什么神奇能力,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她思念父亲、努力破案,两者合一,就成了梦里办案的情节,但这就是她想要的。”在这里,梦不是神谕,梦是野心。小说家和刑警和世人相同,自以为通透如解梦者,皆为梦游者。正如写出《他们》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(Joyce Carol Oates),这样定义作家与梦的关系:“我们也许沉溺于梦境,但绝对不是出于对现实的恐惧或者篾视。我们写作的原因与做梦如出一辙,我们没法不做梦。写作的人是严肃的做梦者。”这是一部推理小说,小说理所当然的推向了犯罪者的谜底,却提供了另一个思考与暗号:“有罪等于可恨吗?”同时,这也不只是一部推理小说,因为它不断给予提示,几近心理暗示。翻开书页,小说之前,你首先会看到“天空是白的,但云是黑的。”这是出自经典法国电影《新桥恋人》里的一段台词——它更是确认彼此相爱的密语,虽然大多数的爱情,总是危颤、疯癫与不公平的。爱这件事,果然与小说很像,可能罪恶,却不一定可恨。本文作者蒋亚妮1987年生,台湾台中人。 摩羯座,狗派女子。无信仰但愿意信仰文字。东海大学中文系、中兴大学中文所毕, 目前就读成功大学中文博士班。 曾获台北文学奖、教育部文艺创作奖、文化部年度艺术新秀、国艺会创作补助等奖项。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《请登入游戏》(九歌), 2017年出版《写你》(印刻), 2020年出版《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》(悦知)。
+ More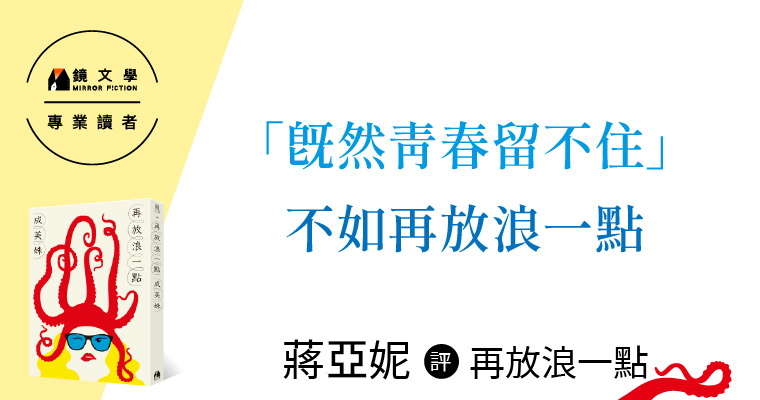
“既然青春留不住”,不如再放浪一点——蒋亞妮读成英姝《再放浪一点》
我很害怕单一化。不管是一件事、一种称呼、一个版块或一类性别,比如“女性文学”、“女性作家”与“女性书写”(替换成同志亦然),但我明白这些存在,依然有其必要性,因为世界确不存在专指男性书写的“男性文学”,我们只能不断催熟“其他”、壮大“之外”。成英姝的最新长篇《再放浪一点》,距前作《寂光与烈焰》整整四年,男赛车手开出记忆的荒漠,这次的小说主角是三个有欲望、有野心的女性。成英姝只使用了一个进行中的“剧本”,便将三者串连。三十多岁的女编剧高爱莫,一直期待写出畅销剧本,却总是心比手高;五十多岁的过气艳星巩丽莲,将最后翻红的机会压在请高爱莫为她打造的剧本上;最后是二十多岁的Z咖女演员林由果,为了演出机会极尽卖傻、卖疯、卖性感,抛售羞耻。不经意处,有著张艾嘉2004年电影《20.30.40》的女性年龄思考,或许一点1994年王晶电影盛世时期《恋爱的天空》(又作《四个好色的女人》)中的自觉与讥诮,偶尔闪过2013年黄真真执导的《闺蜜》里,少数精彩大胆的生动对白,叠影混搭。说穿了,《再放浪一点》是讲女性的小说,却不该被单一化为女性小说,这是我深以为戒的阅读整理。1990年“布克奖”得主,英国作家A.S.拜厄特说过:“如果要做为一个好的女作家,你首先要是一个好的作家,而不是仅仅和女作家在一起,大家只讨论女性的事情。”这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说过的:“在这个世上,我首先得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,然后才是一个作家。”放在一起看,相当有趣。事情的优先顺序永远是,先是一个怎样的人、才是一个怎样的作家,至于性别,万万不需要沦落为少数族群与偏远地区一般的加分要点。成英姝虽然在《再放浪一点》不断拿针戳出女性的血点,像是谈到年纪时,她写四十多岁女人的屁股,会从短裤下缘垂出,但穿的却不是热裤;可四十多岁也不全然缺点,比如女人拉皮:“都说拉皮就要趁年轻,大概四十多岁最好,拉了能定型,还好看,老了才做,三两下就崩坏了。”幽默的最高级是开自己玩笑,这点成英姝与她小说中的三个女人都做到了(换成男性处理就容易落得政治不正确)。如果就只停留在此,三个女人一台戏,就算再加上一个畅销名作家梁梦汝与时尚设计师维若妮卡,五个女人大搞女性主义,唱得也还是过于单调了。还好,成英姝不需要女性加分,她在《男妲》跟《地狱门》等长篇作品里,已经自证这点。不管是暴力、类型、情色与异色,她都玩过了,所以我们必须看进深处,穿越性别、翻玩意识。大家应该都听闻过维吉尼亚·吴尔芙那如当代夏娃宣言般的“自己的房间”,女性(尤其写作者)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,房间需能上锁。不过吴尔芙的原句不只这些,而是:“女性要想写小说或诗歌,必须有五百镑年金和一间带锁的房间。”散文集《自己的房间》出版于1930年前后的英国,作个简单计算,那时的500英镑约等于如今的120万至150万新台币(相近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以上男性年收入)。吴尔芙与她“500英镑说”也非凭空发论,刚好是她姑妈留予她的遗产年金。可惜,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,民国107至108年平均年收入,当代台湾女性大约落在57万至60万间,小说中的三个主角大约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。当我们都少有“500英镑”年收时,就不再写了吗?答案很简单,不管你是男是女、优渥还是落魄,都得要写。反正生活再惨,小说里得暂时靠海苔片、泡面、豆腐撑过生活的女编剧也宽慰自苦地说了:“几个月接不到工作,明明过著清贫的生活,却一点也没瘦,又是一桩宇宙并非逻辑建构的证明。”编剧也好、作家也好、画家编辑老师都是,拿著笔的一个都逃不了,比起性别,《再放浪一点》的主体,更靠近一群无处可归、无路可出的现代人。这不禁让我想到多年前成英姝在“三少四壮集”发表的短文〈我们都太在意永远〉,她写喜欢的作家:“托尔金的世界是一个放置在真实的凡俗的平淡无奇的世界中的箱子,两者平行重叠,当浓雾遮盖了视线,有时拨开那白色的帘幕,就会置身在托尔金的世界中。有一种电影情节,主角意外或者为了某种目的,来到了另一个时空,大部分的剧情,最后都让他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。”这也是我在读这本小说的感受,当我在小说世界、他者时空,游历一场后,却发现听到的全是我自己世界的回音与困境。比如,故事的存在可能;比如,美好的总是往日时光。虽然美国小说家劳伦斯·卜洛克声明:“伪造正是小说的核心与灵魂。”而在一众台湾小说家中,成英姝很高程度地展演了她虚构(Fiction)的能力,私小说的座位,即使你拿著她生平门票一幕幕寻找,最多也只能看见经过了离解、脱墨、洗涤、漂白而还魂的再生纸,前人的名字与笔迹,你找不到。她是罕有地认真说故事的人,为我们展演她精心设计的一个又一个“灵晕”(aura)。灵晕就像故事的入场卷,你得透过它才能真正进入故事氛围。她通过小说中编剧角色的困局,狠狠敲击了当代文学一直讨论不休的:该怎么说故事、还有没有故事,以及有没有人还在说故事?于是在小说故事完结前,她忽然花了许多段落定义“故事”:“故事究竟有没有它自己?那个它自己又是什么,在什么时刻诞生的?人的一生说了数不清的故事,这些无穷的故事散乱,充满矛盾、歧义,它们会被什么指向一处,变成同一个故事吗?⋯⋯事实上,每个故事在当下便已完成了,每一个瞬间就涵盖了过去和未来的可能,在那个点上,它已经是完整的了,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。”成英姝以故事作答故事存在,故事是有可能的,小说依然在说著不同故事与包裹故事,故事里又再藏著些许内在自我。小说随著主线“剧本”的完成,走向结尾,最聪明者显得蠢笨、最痴傻者却看得最清,撕逼的人说不定相知相惜,这样的安排在小说里并不特别,特别之处是成英姝洞悉世情的口吻,当她写道别人教训爱莫的编剧态度时,说的是:“你犯的这个毛病也反映在你的创作态度里,你鄙视陈腔滥调,你对于无论是别人或者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都认为没有价值重复,但你以为真理有多少?”过去了,才有来处可以回头,天真过,也才能说世故的语言。我和小说同时惊觉,现在的所有故事,都由“过往”触发至今,就像五十多岁的昔日艳星高谈自己仍有粉红色乳头一样,看似放浪的全是幻梦。每一个小说的角色都困于旧日,尚未发福的身材也好、捧在手心的爱或是充满可能的未来都结束了,于是小说为他们写下:“以为永远记住我们年轻时的样子,仿佛就能回到过去,但过去就和未来一样,从不在默默那里等待。”说的其实是,往日时光,早已远去。“回不去”的不只叫半生缘,方文山为南拳妈妈写的歌里,那年Lara也唱著:“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,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”小说中的每个人,似乎也都无家乡、无归途。既然无家无乡(也没有吴尔芙说的百万年金)、既然青春终究留不住(也活不成李宗盛一样的成功大叔),成英姝告诉我们,不如再放浪一点,反正,没有从前了。
+ Mo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