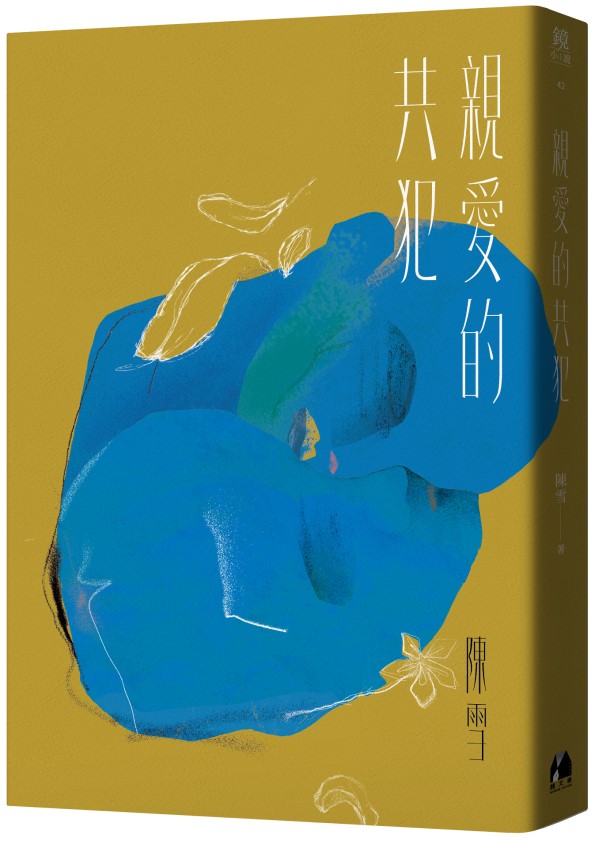无以为家的人——专访陈雪《亲爱的共犯》
文|翟翱
2021-01-26
陈雪一直在浪头上。从90年代开始,她是弄潮儿也是酷儿,时代迎面而来,便理所当然的用尽生命书写。我问陈雪,“现在还有人用‘酷儿文学’称呼你吗?”她回答,“很久没听到了,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是什么。”
2019年陈雪随同婚法制化结婚成家。看起来,90年代那个披酷儿文学先锋标志上阵的陈雪已远。然而要到新作《亲爱的共犯》,我们才发现成家后的她成了潜行者,矗立一座家,悄悄从内引爆。
“如果没有原生家庭,只能自己去寻找家的话,这个可能性是什么?”陈雪说。
这或许可从她在小说前引用的电影《新桥恋人》台词“天空是白的/但云是黑的”看出端倪。盲女与流浪汉在废弃的桥上相遇,不见于社会的爱只能在不是家也非一般人栖身之所的桥上滋长。
当爱始自荒芜,家的意义便同步塌缩。
亮丽的家埋藏著什么
过去陈雪创作出一个个罢家女孩(藉逃离原生家庭,反省亲密关系),现在她一手写恋爱课散文,一手搭起《摩天大楼》,具象化社会结构与受困其中的人;再来她搭建《无父之城》,搬演终极的暴力——白色恐怖。
《亲爱的共犯》以一桩富二代绑架案开始,自幼失父的女警“周小咏”进入豪门调查,却发现侯门似海之外,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位置也开始混淆不清,最终成为《白夜行》式爱与恶的辩证。我们到最后才明了爱是救赎,也是诿过。
陈雪在《亲爱的共犯》里搭建一个整洁美满又安康的家,里头的人却不幸福。再明亮宜人的家对不幸的人来说,也只是有屋顶的天葬。
《亲爱的共犯》触及不同阶级对家的想像,来自陈雪过去对家的不满及憧憬,“小时候我很讨厌家里的巧拼跟三层柜,心想为何大人都买这种东西。后来我认识一对夫妻,他们家充满廉价家具,毫无美感可言,我却感到家的感觉。渐渐的,我发现你去很高级的地方,即使像饭店美好,但你不会称为家。”
“现在大家常常谈断舍离,想要干净清爽的家,更好的生活,然而里面的人的状态是什么?当我们期望干净整齐的美感,就很容易不自觉的高人一等。使用美的东西,其实不会让人心里变美,更多时候是为了隔开混乱与肮脏,同时画地自限。”
因此,《亲爱的共犯》开篇便是富豪“张大安”盖的“白楼”。陈雪这样描述:“一栋白色的建筑在夕阳映照中,呈现出几近金色的光辉,倘若有一双眼睛从空中俯瞰,将会看到那一栋市区巷弄里的独栋楼房,在一片灰色乐高玩具堆起的矮矮楼房中,站立著白色的庞然大物。”
在不成家的地方守望
陈雪写家,是颠覆,同时也小心呵护另一种家的可能。《亲爱的共犯》另一个重要场景是育幼院。陈雪说她一直对育幼院很感兴趣,小时候常觉得自己会被送到那,“因为我父母曾经分开,我始终有种不安全感。那时候《小甜甜》正红,我跟小甜甜一样有雀斑,大家就叫我小甜甜。可是卡通里小甜甜待的孤儿院很温馨,我的家却不成家了。”
“我对特定空间著迷,总想著这里面住著怎样的人?”从《摩天大楼》到《无父之城》,陈雪在封闭的空间中试验人性。在《亲爱的共犯》里,人物则被放到两个极端——白楼与育幼院。
育幼院培育没有家的人,那些人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,会是犯罪者的面貌吗?答案当然绝非如此简单。这便碰触到小说另一个主题——爱与恶的等值。
“爱一个人何时会变成恶或罪?”陈雪问道。
《亲爱的共犯》以绑架案开篇,然而陈雪志不在写复杂的犯罪,“我不是写推理,小说里的杀人都来自人性,而非一个哏,只是想让人猜不到。”《亲爱的共犯》之前,她其实想改写真实刑案,但发现这些案件原因看起来都很简单,“可是人是这么复杂,这些简单或许有他们无法言说的部分,我想知道人在怎样的情形下会杀人。”
“透过小说,我补足真实案件我看不到的复杂面,更千丝万缕的看待犯罪,试著找出一个人的生命在何时产生分歧。”
因此,《亲爱的共犯》看似是侦案故事,到头来却展示——陈雪习惯用“展示”描述小说里的道德困境——令人怵目惊心的悲剧,“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改变,活得很小心,往往还是被命运拉了过去。你想摆脱过去的恶,可是挣扎的同时也沾染了恶。”
当暴力散发甜腻滋味
如何书写恶,涉及陈雪近年关注的议题——暴行。“这几年,我一直想写暴行,施加于人却无形的暴力,例如控制与剥夺。吊诡的是,这其中有个反复的模式,伤害之后又呵护。施暴者都有一套说词,‘我是为你好’、‘连你都不相信我’等。我想展示这种暴力的形成,以及它如何黏著人。”
大至国家机器,小至亲密关系。暴力深入脊髓,甚至散发甜腻的滋味,教人错觉是爱。《亲爱的共犯》里的许多人物正是透过家这个结构,用爱去实行错。陈雪透露,她曾经历一段有言语暴力的亲密关系,“对方一下贬低自己,一下贬低我,让我处在是非对错难分的处境。我一直不愿相信自己是受害者,直到对方动手。”
“很多时候,爱是只有一个信徒的邪教,对方成为你的教主。”
过去陈雪小说常出现青春女孩献祭的模式——女孩受了伤,用自身的不幸见证社会的残酷。然而陈雪说,“这一次我的小说人物的爱没有荒芜,还有能力并努力去爱。”
“不健全的生命,不会去爱。然而我们从小到大会受到各种伤害,因此我们怎样通过伤害反过来肯定自己,而不是怀著负罪感。”《亲爱的共犯》一方面毁家废婚,一方面展现了最纯净的爱。
陈雪写恋爱课散文,帮助读者经营亲密关系,自认写散文跟写小说的人格不同,我好奇两者差在哪?“写散文比较接近我自己,写小说的‘我’很淡;写小说比较能把人放到极端,写散文是中间值。”不过《亲爱的共犯》最后其实带著异常温柔的质地。
对此,陈雪说或许是自己有了家庭后,对家的想像更有自信。“我发现家未必要在一个房子里,也可以有照顾与归属感。”《亲爱的共犯》是桥上的孩子长大了,曾经无以为家的人回头探望现在无以为家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