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陌生又熟悉的文字創作,重新認識客語——作家張郅忻的客語文學探索

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「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」,邀請七位知名創作者參與,以一年為期,創作客語小說、散文與詩歌,包括小說家李旺台、甘耀明、高翊峰,散文家吳鳴、張郅忻,詩人羅思容、張芳慈。期待客語成為當代的文學語言,激發客家文化的生命力,讓客語延續綿長。
七部作品將於2026年(民115年)發表,鏡文學特別在創作中期採訪這七位作家,談及客語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,以及客語創作為作家們帶來的思考與啟發。
張郅忻是少數能流利「講客話」的七年級客家作家。生長在客家大家庭,又來自新竹這個海陸腔大本營,縱使父母輩經歷「禁說方言」的時代,客語依然是當地流通的重要語言。
她又是長孫女,因為父親與她的生母在她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離異,她從小被阿婆帶大,也跟在阿太、阿公這些家族身邊轉,每次阿太和阿婆婆媳倆吵架,都用客家話抱怨給這個小女孩聽,要「毋識客話」也不容易。
不過,用客字寫客語,對張郅忻來說,是對母語、對家族故事的重新認識。
「一開始寫的時候,我沒有刻意查客語字典,直接以發音和印象去猜大概可以用什麼字。我不會特別講究,有些客語字我自己知道,有些則是習慣的諧音字,覺得用諧音去表達,好像就差不多。」
後來,張郅忻在大學的客家系短暫工作半年,學校老師研究客語字、編客語辭典,她便跟著學,寫專欄文章時,也就開始在意客語正字,回頭找自己曾經聽過、卻不一定知道怎麼寫的客家詞彙,這才發現有些詞跟她原本的印象很不一樣。
 ▲張郅忻將過去熟悉的客家詞彙用客語正字書寫,有許多新奇的發現。
▲張郅忻將過去熟悉的客家詞彙用客語正字書寫,有許多新奇的發現。
例如「logˋ sienˇ」(海陸腔)這個詞,張郅忻從小聽阿婆用這個詞形容她的父親,像是在說父親因為過度天真,行事不夠謹慎,久而久之覺得這個詞應該帶有負面的意思,一開始猜測應該是寫作「落險」。沒想到客語正字竟然寫作「樂線」,就是生性樂觀的意思。
張郅忻笑說:「我知道在什麼情境可以用這個詞,但我不知道要怎麼連結到它的文字,這次看才嚇一跳,文字看起來好正面喔。」內心的疑惑也隨之解開:原來阿婆可能不是在數落父親過度天真啊。
她把這份感觸化做客語散文〈樂線〉,收錄在這次受客委會與鏡文學邀請參與的「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」的散文集《覓蜆仔》裡。感覺陌生,又很熟悉,一個個存在於張郅忻記憶中、有聲音卻沒有形狀的客語詞,從抽象到具體,終於找到屬於它們的文字。
長大才發現客家人是少數
由於客家庄很多人跟原住民、新移民等族群通婚,在張郅忻成長的過程中,家族有許多不同語言;有主要講的海陸腔客語,也有太公(阿公的父親)和來自印尼的客家人阿妗(嬸嬸,海陸腔:a+ zim)講的四縣腔;另一位阿妗是越南人,父親第三段婚姻的對象是阿美族人,妹妹的婆婆,則是與客家人結婚的泰雅族人。
學老話(台灣台語)主要存在於童年記憶中電視節目或廣播的流行娛樂裡,多少會跟著學到一點點。尤其家中曾經在湖口經營西餐廳,當時流行餐廳裡要有卡拉ok,家人常常會跟著唱〈雪中紅〉、〈針線情〉等台語情歌,看電視播的台語八點檔。
長大後離家,到高雄念書、工作,張郅忻才驚訝地發現客家人其實是少數,學老人其實比較多。
張郅忻之前在高雄的工作,需要接民眾打來的電話,「偏偏打來的民眾幾乎都講台語,我只好用很破的台語講,同事聽不下去,就會說:你把電話拿過來好了。」後來全家族也只有她是跟學老人結婚,公婆的家族也幾乎都是學老人。
 ▲張郅忻長大後才發現客家人是少數,感受到客家的獨特。
▲張郅忻長大後才發現客家人是少數,感受到客家的獨特。
例如,過年期間,阿婆通常會準備她愛吃的糟嫲肉(海陸腔:zoˋ ma ngiug)。「糟嫲」是將釀酒所剩的糟粕,與肉類攪拌調和而成。張郅忻的阿婆做的是糟嫲雞,「結婚後,阿婆每逢過年還是會寄一整隻糟嫲肉給我,看起來就是整隻紅通通的雞,但我過年在公婆家過,全家族除了我沒人敢吃。我就跟阿婆說,寄一點點就好,只有我一個人吃,很孤單。」
還好,張郅忻的兩個小孩出生、成長後,她驚喜發現大兒子跟她一樣喜歡糟嫲肉的滋味,「我很開心終於有人跟我一起吃,有伴了!」
另一個差異是「了少話」(髒話,海陸腔:liauˊ shauˇ voiˋ)。
無論是哪個族群,都有很多人習慣講髒話,也常被當作「發語詞」使用。張郅忻在創作裡描寫客家長輩的互動時,也會視情境將客語「了少話」寫進對話中,呈現地道的客家感覺。但相較於台語的髒話,客語的髒話比較少人聽懂,「如果跟非客家人講一句客語髒話,對他來說是沒有感覺的。」
不管是「糟嫲肉」或是「了少話」,飲食、語言這些客家文化的符號,對張郅忻來說,隨著年歲漸長,逐漸成為一種特別的象徵。
「當你發現自己跟別人好像有一點不一樣的時候,就會突然感受到自己是客家的;是從一個客家小鎮長大的人。」
在阿婆忘記之前,把回憶寫下來
在客委會與鏡文學邀請參與「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」的七位作家中,張郅忻是最年輕的一位,但創作力豐沛,已經累積許多作品,類型更囊括小說與散文。
她在散文集《孩子的我》記錄大兒子的嬰兒時期,也追憶自己童年的故事,長篇小說「客途三部曲」《織》、《海市》、《山鏡》中,則融入阿公、媽媽、爸爸的人生經歷作為靈感,《山鏡》更獲得2024年台灣文學金典獎肯定。
2024年出版的《秀梅》,則是一本寫給阿婆的情書,她將從小帶著自己長大的阿婆做的21道菜,寫成客家女性堅毅的生命故事。
在寫《秀梅》的同時,張郅忻的大姑姑和父親接連過世,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,讓阿婆出現了失智的徵兆,讓張郅忻忍不住焦急,想在阿婆還記得的時候,完成這部作品。
從《秀梅》開始,張郅忻就刻意將「客語字」放入創作中,不只對話,連描述的情節都用客語字,幾乎有六成內容用客語呈現。她也刻意只放少量註釋,希望讀者透過閱讀自然理解客語詞彙的意涵。「我其實也很掙扎要不要用這麼多客語,但《秀梅》是以我阿婆為原型的角色,她就是用客語思考、用客語對話,如果都換成用華語寫,這個角色就好像不是她了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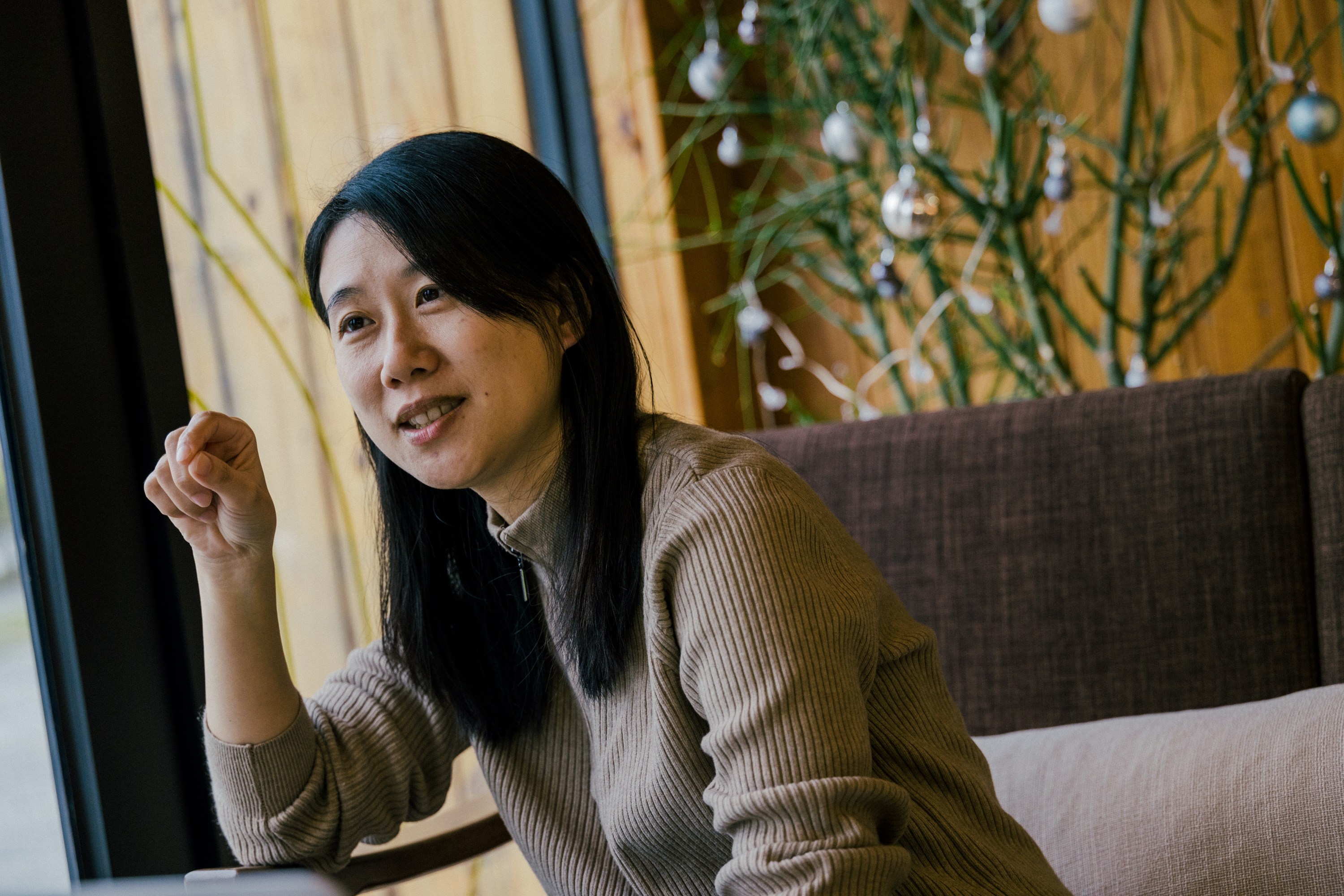 ▲對張郅忻而言,寫客語散文就像在泥地裡摸蜆,找尋珍貴的客家記憶。
▲對張郅忻而言,寫客語散文就像在泥地裡摸蜆,找尋珍貴的客家記憶。
接到客委會與鏡文學邀請,參與「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」時,她一邊學習寫客語字、構思創作,一邊想到的是童年「覓蜆仔」的經驗。對她而言,寫散文就像是在泥地裡摸蜆,可能要摸索很久,才會找到一顆珍貴的蜆,「透過寫散文,我在打撈過去的經驗和語言的記憶。」
「如果沒有記錄下來,就會忘記原本怎麼說。因為講了就過去了,也不會記得這個詞是怎麼來的。」例如張郅忻童年常聽阿婆稱計程車作「嗨呀」(發音近似:haiˋ yaˇ),一直以為是客家話,長大後才發現是日語「ハイヤ」(haiya),也跟英語「hire」有關。一個常見的詞彙,背後竟然有這麼多層文化轉譯。
「阿公那一輩人,還能用客語讀漢文,能隨口就說出有典故、韻腳的客家諺語,但到爸爸、叔叔這一代就不會了,再到我,雖然日常會話沒有問題,但像是有些植物、動物的名稱,我就不熟悉。」
張郅忻看著客語從阿公阿婆那一代,到爸爸媽媽、叔叔阿妗這一代,能嫻熟運用的範圍愈來愈小,再到她,若非從小被阿公阿婆帶大,她這一輩已經不太講客語,都講華語了。
從童年練拳回憶,理解族群衝突
張郅忻的第一篇全客語創作是短篇小說〈打拳頭〉,曾獲2023年台灣文學獎「客語文學創作獎」,描述從前芝芭里的客家庄為了防範福佬人來搶水,決定重金禮聘師傅,從芎林翻山越嶺來教大家練客家拳。兩個喜歡打拳較勁的童年玩伴,長大後一個繼續練拳,一個決定升學,人生道路漸行漸遠,卻還是記得童年練拳的夥伴情誼。
張郅忻先用華語試寫,但怎麼寫都寫不好,於是改用客語寫,直接描述角色的對白、動作,發現很適合短篇小說的節奏。為了全篇用客語,不知道怎麼描述的詞彙,就回去問叔叔,也不能直接把華語翻成客語,她要先敘述情境和狀態,交代前因後果,再問叔叔會怎麼用客語描述,這樣才會得到自然的結果。
面對陌生又熟悉的語言,反而能用更直接貼切的方式敘述。「因為太熟悉華語,每一個說法,都可以找到一個形容詞、找到比較漂亮的用法,但對這篇短篇小說來說卻不夠生動。用客語寫,我反而可以自在地丟掉那些字,從頭來過,用客語的語感思考。」
 ▲藉由童年學客家拳的記憶,張郅忻追溯客家人與其他各族群在不同時代的紛爭與互動。
▲藉由童年學客家拳的記憶,張郅忻追溯客家人與其他各族群在不同時代的紛爭與互動。
〈打拳頭〉的靈感來自張郅忻的家族記憶。
當時張郅忻剛剛搬家到桃園青埔一帶,叔叔從新竹來拜訪,聊起家族長輩故事。叔叔告訴她,以前窮人家會租田來耕種,她的阿太租的田地,就位於以前的芝芭里,離她住的地方很近。
芝芭里有很多閩南、客家勢力交錯的地段,不同族群之間為了灌溉農地,彼此搶水,但因為閩南人多,客家人常常會輸,於是張家的長輩就去很遠的地方聘請師傅,讓全家族男女老少都來學客家拳。
這勾起張郅忻的童年記憶,她小時候也曾跟著家族親戚短暫學過客家拳。「那時候正在推廣社區營造,希望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。叔公本來就在開國術館教客家拳,就去公廳(祠堂,海陸腔:gungˋ tangˋ)教大家。阿公覺得練客家拳對身體好,又可以防身,就帶我和妹妹去學。」
客家庄練客家拳,表面上是強身健體,背後卻呈現出客家人與各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。
正好張郅忻因為工作,接觸到客家古宅「李騰芳古宅」和「金廣福公館」的歷史。其中「金廣福公館」更是閩南人和粵籍客家人合作的墾首,在新竹北埔半山處一帶掌握很大的權力,不只客家人與原住民爭奪資源,清政府又不安墾首勢力過大,想裁撤各地墾首隘首,「金廣福」斡旋於原住民與清政府之間,發生許多流血鬥爭的故事。
張郅忻將這些族群歷史虛構成短短的故事,也加入自己的心得,一同收錄在散文集裡,希望將客家前輩的事寫下來。
「不同時代的客家人與各族群的衝突,好像是以前學校課本比較沒有教的。我想藉寫作的機會,去理解過去的客家人建立自己家園的過程,也試著從女性的視角敘述。這些族群相爭的故事,也都是廣義的〈打拳頭〉。」
傳承客家記憶,與兒子「慢慢行」
除了寫過去,張郅忻在散文集《覓蜆仔》也寫現在,寫自己與先生和兩個倈仔(兒子,海陸腔:laiˇ er)一起生活、一起「慢慢行」的日常。
 ▲提到同樣有個客家味蕾的大兒子,張郅忻笑得開懷。
▲提到同樣有個客家味蕾的大兒子,張郅忻笑得開懷。
出身閩南家庭的先生,就算聽不懂客語,需要她當翻譯,也還是能與她一起欣賞動人的客語歌。張郅忻的大倈仔,出生在客語、台語各半的家庭,也從她身上傳承許多客家特性,例如同樣愛吃糟嫲肉的客家味道。甚至客家「雞酒」拌飯,大倈仔可以狠狠吃掉兩碗公,被親戚戲稱是「飯囤」(punˊ tun,張家習慣形容「大食客」的說法)。
小學有母語課,班上只有她大倈仔和另一位同學選客語,某天老師請張郅忻勸兒子代表班級參加客語演講比賽,他害羞,不願意參加,跟媽媽抱怨:「我覺得我好可憐,生在一個客語家庭。」
張郅忻描述到這裡,自己也笑岔了氣:「沒辦法,全班就只有兩個會客語,要參加客語比賽,當然只有他們兩個可以輪著去啊!我就跟他說:你現在一定要好好學,我們客語已經快要沒有了……」
對張郅忻而言,客語不只是從過去回憶中掏洗的蜆仔,她也希望能用客語記錄自己與下一代的客家故事。
「以前寫《孩子的我》,就算是孩子長牙之類的日常瑣事我也寫,當時也懷疑這麼小的事值得寫出來嗎?十年過去,現在回頭看,發現有這樣的紀錄非常重要。」
「我也想把此時此刻的事用客語寫下來。未來回頭再看,也是『覓蜆仔』的蜆仔,是很珍貴的事吧?」


▲張郅忻創作全客語散文集《覓蜆仔》,希望將客語傳承到下一代。
撰文 許文貞 ◆ 攝影 桑杉學 ◆ 責編 林潔珊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