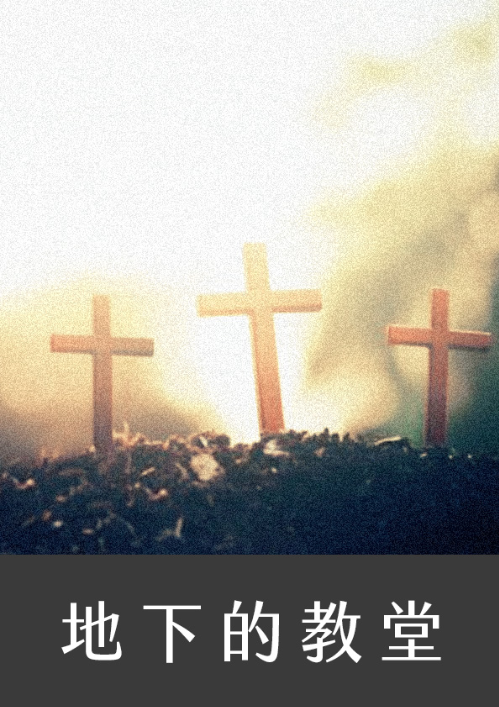【作家特写】在现实的废墟中制造天堂 议题派小说家甘弟
文|翟翱
2018-11-19
 立即阅读:《千纸鹤:秘密》
立即阅读:《千纸鹤:秘密》
甘弟本名邱宗翰,写有《百工之人》、《千纸鹤》等社会议题强烈的长篇小说。身为小说家,他积极介入现实,用文字直逼各种议题,包括核安、废死、长照等。然而,如此入世的写作姿态,其实来自他出世般的苦行生活。
过分认真的甘弟,使他的写作与生活都成了修行。
他曾闭关四年,断绝与外界所有联系,每天只写小说,用脑过度,患上头痛毛病;他奉行永续和谐理念,吃全素,还有全套环保器具,环保吸管、环保筷,以及三组环保袋交替使用。待人接物他也一贯决绝。朋友酒驾,他送对方一组佛教乐器——磬,希望友人振聋发聩。岂料对方再犯,他便与之决裂。
 甘弟在补习班教国文,他说自己是「说书人冒充国文老师」,透过讲述一个个故事让学生对知识与世界充满好奇。
甘弟在补习班教国文,他说自己是「说书人冒充国文老师」,透过讲述一个个故事让学生对知识与世界充满好奇。
对此,甘弟只说:「我宁愿孤独也不能违背自己的理念。」结果是他的朋友少到结婚时只发了四张男方亲友喜帖。孤独的时候,他用写作顶住大而残破的世界。其实,他身殉文学的态度,从笔名就看得出来。
小说是自我追寻之路
访问一开始,我便好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笔名从何而来。聊著聊著,我们岔题了,甘弟复主动提起这个问题。他说来源有三,首先是他的精神导师──甘地。他用这个名字写作,希望每次见报都像在宣扬甘地的精神。此外,「甘」也来自《阿甘正传》男主角──阿甘母亲要阿甘遇到问题时就往前跑,他便跑了一生的长度,「很多人觉得阿甘很笨,但我觉得这是坚持,不是笨。」就连笔名也是他自我砥砺的工具。至于最后的弟字,则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么。
甘弟现于台中教补习班。之所以选择补教业,也是因著写作,「这是花最少时间可以获得最多金钱来支持我写作的行业。」甘弟总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:「说书人冒充国文老师」。然而,说书人想说的是自己的故事,「在课堂上我说故事,但不是我想说的故事。既然我教书已为了迎合市场,写作时我只想写自己想写的。」
正因如此,甘弟笔下的故事尽管千回百转,仍往往是自我追寻与辩证的过程。长篇《百工之人》讲童年悲惨的捡骨师意外寻得生父遗骨,既寻回自己的前半生,也为作恶多端的父亲赎罪;《千纸鹤》藉一桩老人院命案带出母女和解的故事。命案不是重点,案件周围的情理才是小说家著力之处;爱与孤寂与失落,放在罪与罚的天秤上,该如何衡量?《千纸鹤》里看似难解的习题,却成为甘弟目前最满意的作品。此外,还有短篇〈地下的教堂〉、〈凯达格兰的独舞〉、〈有福〉等,分别聚焦劳工、兰屿核废料、核安议题。
写出蒙尘角落的故事
甘弟的小说总可见若干社会议题,他说自己最崇拜托尔斯泰,写作是「用文学记录社会运动,把很严肃的议题说得很精采。」他住在图书馆附近,不是在埋头写作,就是在图书馆翻文献找资料,或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。
我提到他的若干小说让我想起黄春明,同样聚焦底层,也往往让他笔下的小人物在黑暗中一步步通向有光的所在,「上层的成功故事天天都在流传,底层发生什么事却没人看见。如果我不去写,可能就没有人在乎了。我甚至想写动物的故事,为动保说话。」
 「我宁愿孤独也不能违背自己的理念。」甘弟把自己的生活与写作都变成了修行。
「我宁愿孤独也不能违背自己的理念。」甘弟把自己的生活与写作都变成了修行。
是否透过小说向读者灌输自己的价值观?甘弟说,「我想呈现真相,写完后我自己会有答案,至于读者,就让他们自己领会。在我的小说里,没有主要的声音,每个角色都有发言权。」好比《千纸鹤》里的法庭攻防涉及死刑议题,甘弟承认自己支持废死,「我不怕让人看见自己的观点。做一个负责任的作家,必须有勇气提出你认为对的答案。」
于是,我们谈到文学如何与现实重叠,小说太贴近现实,是否便成新闻照抄,以及小说会不会与非虚构文学没有了区别?「当现实与戏剧性冲突时,我会选择后者。对我来说,报章杂志仍有破口,得透过小说去探索。」我想起佛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里申明的:「小说比历史更真实,因为它超越了可见的事实。」相较于真实,甘弟同样追求说故事的力量,「故事只要存在,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读,藉此回到那个时空。」甘弟说,他的小说与非虚构文学分进合击。
甘弟用小说发声,但小说的力量在当代恐怕已式微。我们聊到台湾近期以文学改变社会的例子,两人脑中顿时一片空白。不过,甘弟举了一个反例。几年前加拉巴哥象龟亚种之一,平塔岛象龟仅存的「孤独乔治」死亡,该物种遂宣告灭绝。许多人以此为创作主题,看起来是悼念一个物种的消亡,然而更多是因为「孤独乔治」带来的孤寂感太过强烈,让人浮想联翩。甘弟说,文学处理议题不免走向抒情,最后往往也只能抒情式结束,他自己则尽量避免让小说流于滥情的同情。
或因如此,写作路上的甘弟是孤寂的,他说自己写小说没有市场考量,冷门也没关系,「我是我自己最忠实的读者,因为我写的都是我自己想知道的事。」
创作是欢愉也是赎罪
甘弟的创作之路有自我质疑,也有至高无上的成就感。他说写小说可以给他极大的快乐,「我只是在抄脑中跑出的文字,彷彿我身在其中,听到小说人物的对话。写作让我上瘾,非常痛快。」他形容写小说写入神是「上帝亲吻的时刻。」他的小说瘾头多重呢?甘弟当兵时在野地出任务,因为想写小说,跑到连长的指挥所,戴著钢盔,用NOKIA手机3310当光线就开始写,同袍看到还吓了一跳。
 甘弟关注时事,除了写作,也上街头;对他而言,两者有同样振聋发聩的效果。
甘弟关注时事,除了写作,也上街头;对他而言,两者有同样振聋发聩的效果。
不过,创作不是全然幸福的一件事。甘弟把生活过得像是修行,写作对他而言,也是修行的一部分,「写作对我是赎罪,既然苟延无耻的活著,就要靠写作救赎。」
创作之于他的矛盾,或许从他笔下的女性可窥见一二,「我小说中的母亲常常是妓女或瘫痪者,因为我的家庭非常复杂,我妈在酒店上班,我爸是警察,我有两个姊姊,一个同母异父,一个同父异母,后来才发现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,我妈还有很多『叔叔』,我爸也有很多『阿姨』。我妈上班时间很晚,小时候看到她,她几乎都在床上睡觉。」母亲对甘弟来说,是难解的存在。他说母亲有躁郁症,全家不知该如何面对,便逐渐瓦解;献给妈妈的小说写完,想给她看,「但想起她带来的痛苦,我犹豫了。」
小说家瑞蒙卡佛谈人生,说:「对大多数人而言,人生不是什么冒险,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。」甘弟投身洪流,透过书写,让自己也变成洪流的一部分。谈及他计画中的大长篇小说《人造天堂》,是以巡礼各国各地的方式检视人类的存在,也是他永续、和谐理念的延伸。
「我们制造了一个废墟,要怎样让它变天堂?」这是小说家甘弟的天问了。